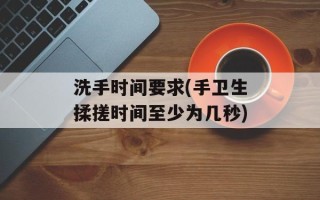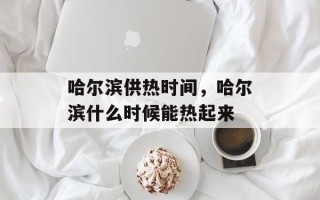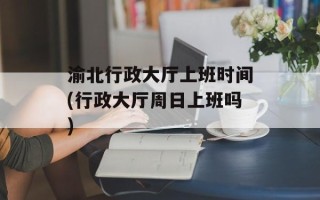中国人的早餐中,标配的就是豆浆油条,尤其是现在早上如此的冷,早上就想要喝一点热乎乎的,豆浆这样的热饮,不管是在北方还收在南方都是不会让人拒绝的美味。正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喝豆浆,所以就产生了很多 *** 豆浆的小家电。
现磨豆浆是1900多年前的西汉淮南王刘安 *** 的,所以说已经有接近2000年的历史了。豆浆也是一种老少皆宜的营养食品,豆浆的 *** *** 也简单,已经从最早的研磨黄豆的粉碎机,到后来的一键式 *** 作的豆浆机,到现在的破壁机和免浸泡的可以磨干豆的豆浆机,真的就是发展的越来越方便了。
不过也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反映,虽然在家里面磨制豆浆很方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的豆浆就是不够顺滑,甚至豆浆打出来喝起来还是发苦的,跟外面卖的那种豆浆就是不一样,那么该如何正确的打豆浆呢?该用湿豆还是干豆来打呢?
区别:
干豆:大家很多人都认为用干豆来打豆浆营养成分保留得比较多,豆浆机虽然可以打干豆,但是刀头损坏快,而且打好的豆浆有明显的渣。豆腥味很浓,直接打的豆浆也不够香醇,有一些豆腥味,所以不建议用干豆来打。
湿豆:用湿豆来打豆浆最明显的就是出浆率比较的高,而且豆渣也减少了。浸泡时间越长,出浆率越高,也有利于营养成分的释放,口感比干打要好很多。但是黄豆用温水泡过之后,很容易会泡发出一种苦味,也是很多小伙伴跟我反映打出来豆浆喝起来苦的原因。
正确的 *** :
我们先来把黄豆提前用清水浸泡一个晚上,这样浸泡过的黄豆在打豆浆的时候出浆率会非常高,而且打出来的豆渣也会非常少,下面就是重点了,不要立马把浸泡好了的黄豆扔进豆浆机里面。
而是把浸泡好了的黄豆放进锅里面煮一下,大约是煮个15分钟左右,不煮的话也可以改成蒸,时间是一样的,重点在于用熟豆来做。用煮熟了的豆子再来打豆浆的话,不仅口感细腻,喝起来也没有苦涩感,这个办法大家可以试一试,这样一来,豆浆不仅味道香浓,口感也更加的丝滑。
除了这些,在豆浆机的挑选上面也要注意,我家一直用的是臻米的mini破壁机,正好可以打一人份和两人份的量,特别的方便,而且别看它这么轻巧,确有名副其实的破壁功能,打干豆不在话下,打出的豆浆不用滤渣也很细腻。
它的工作原理是一边煮一边破壁,可以快速出浆的同时,也能保证彻底的熟化。而且刀头的部分可以打开,清洗更简单。打蔬果汁也很方便,冷热都能用。
上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正确打豆浆的 *** 了,你还有什么意见分享出来,没有试过的小伙伴赶紧试一试, *** 绝对管用。
导读:豆浆是中国最传统的饮品之一,相传是1900多年前的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发明出来的。而豆浆还是营养价值超级高的一种饮品,特别是小孩和老人常喝,能提高免疫力,所以我每周都会自己打1-2次豆浆给家人喝!而现在市面上的一小杯豆浆,至少需要2元1斤,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己在家打豆浆。而在家打豆浆的 *** 有很多,比如有人用破壁机,直接将干黄豆放入到机器中,然后按定时,第二天一早就有热气腾腾的豆浆喝,还有人用榨汁机,将黄豆泡一晚上后,然后把黄豆榨成汁,接着将打出来豆浆放入到锅中,大火煮开即可饮用。
而用破壁机和榨汁机打的豆浆,它们更大的区别是:一个可以用干豆,一个必须用湿豆。而不少人反映,自己在家用破壁机和榨汁机打的豆浆,总是没有楼下早餐店的好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用干黄豆直接打豆浆,会导致豆浆的豆腥味比较重,而用泡胀后的豆子打豆浆,豆浆不是很浓!而胡师傅曾经也做过2年的早餐,因为太辛苦,就没有做了。在我宣布关店的那天,不少老顾客来我店,我都请他们喝一杯豆浆,当时不少长辈,都希望我把打豆浆的做法告诉他们,而我也提前准备了一些宣 *** 给他们,当他们看我的 *** *** 后,都说没想到,一个最简单的饮品,也有这么多技巧。
而我的豆浆做法,和大部分人的做法都不一样,因为打豆浆,用干豆和湿豆都是不对的,而我打豆浆一般都是用的熟豆,接下来我就把正确豆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按照我的 *** 做,保证豆浆能做的又香又浓。
【原材料准备】:黄豆150克、小苏打2克、白砂糖50克、清水适量。
【豆浆正确的做法】:
之一步:首先将黄豆、小苏打一起放入到冷水中浸泡6-8小时,直到黄豆完全泡胀,然后再将泡胀的黄豆冲洗2遍即可备用。
第二步:锅中放入适量的水,把水煮开后,将黄豆放入到锅中,大火将黄豆煮5分钟即可捞出。

第三步:将煮熟的黄豆放入到榨汁机中,同时加入适量的冷水,将黄豆打成浆后进行过滤,只留豆浆备用。
第四步:将打好的豆浆放入到锅中,大火将豆浆煮开后,然后将白砂糖放入到锅中,继续煮1分钟即可饮用。
【打豆浆的注意事项】:
1、浸泡黄豆时,建议大家放少许的小苏打,因为小苏打可以不仅减少黄豆的腥味,而且还能使黄豆尽快地泡胀。
2、煮黄豆时,只需要将黄豆煮5分钟即可,千万不要久煮,因为煮的时间过长,黄豆就会完全熟透,这样就会导致黄豆不能出浆。
3、因为黄豆在打浆之前,黄豆已经完全煮熟后,所以我们再煮豆浆,只要豆浆煮沸腾后,继续煮1分钟即可饮用,不必久煮。
大家以后打豆浆时,用干豆还是湿豆都是不对,正确的做法是将黄豆煮熟后再打浆,这样做的豆浆才又香又浓。本文是胡师傅原创的图文,后续胡师傅还会给大家讲解更多做菜诀窍、养生菜谱给大家,感谢您的观看,如果今天的文章对您有帮助,那就点一个关注,点一个赞,感谢您的支持。
别看不起豆浆粉了,它可能比现磨豆浆更好#古籍守护人#饮用豆浆从宋 *** 始出现,元代成为日常饮食。在此之前出现的豆饬、豆饴、豆羹、豆汁、豆粥、豆糜等物均非豆浆,中古时期并没有饮用豆浆的习惯。考古出土的早期石转磨在结构上类似湿磨,但并不能证明其用途是磨制豆浆。豆浆成为食品并不在豆腐发明之前,早期豆腐可能并不是由豆浆 *** 。研磨豆浆的技术条件早已具备,但饮用豆浆开始于宋元时期城市经济繁荣之后。体现出技术基础满足并不一定出现技术创新,技术发明的推广更需要考虑技术之外的社会因素,中国古代“超稳定饮食结构” *** 了豆浆的发明、推广,这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观察并思考古代科技。
豆浆,又称豆乳,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种美食。大豆研磨之后再过滤煮熟,就制成了我们日常饮用的豆浆。古人亦能享受豆浆的美味,但我国先民究竟从何时开始将豆浆作为日常食品,该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梳理豆浆的起源与发展,不仅可以明晰豆浆的历史,同样有助于认识豆粥、豆腐等食品的产生发展。既往研究中涉及豆浆起源的不可谓不多,提出了许多观点与证据,但多有可讨论之处。本文首先对既往观点作一辨析,在此基础上重新检核材料,分析豆浆及其相关食品的名与实,探讨豆浆从技术基础的形成到推广为日常饮食这一曲折复杂的历程,并尝试由此揭示古代科技发明与饮食文化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既往豆浆起源研究的辨析
目前所见的研究,几乎全部认为至少在汉代豆浆已经出现。其论据可分为三种:一是文献中的“豆浆”记载;二是由豆腐的出现反推豆浆,三是考古出土的石转磨利于磨制豆浆。本节先分析前两种证据。
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提出《盐铁论》中的“豆饧”,应当是一种甜豆浆或豆腐脑。原文“豆赐”最早由卢文弨校为“豆饧”,各家对其观点不一,《盐铁论校注》的校勘记中列举“锡”“饧”“肠”各种观点均有,是否应为“豆饧”不为确论。王佩诤认为其应为“豆豉”之误。此外,陈直从对仗的角度提出“胹羔豆饧”应为一动词领三名词,“羔为糕字之省文,豆作粉饵,饧为饴糖,属于小食类,皆烂熟以食也”。还反驳了王佩诤的观点:“豆豉”不须研磨;“粉饵”则是豆粉制成的糕点,与豆浆无干。以上诸说各有其道理,但均为历代注家对“豆赐”含义的猜测,显然不能作为证明豆浆或豆腐存在的有力证据。
即使“豆饧”的确存在,此物也不会必定是豆浆或者豆腐。《释名》曰:“饧,洋也。煮米消烂,洋洋然也……饴,小弱于饧,形怡怡然也。”两物密切相关,因此“豆饧”与“豆饴”应当比较接近。《太平御览》引《苍颉解诂》谈道:“饴中着豆屑也。”《玉篇》又曰:“饴,和豆也。”可知所谓“豆饴”是“饴”添加豆屑之物。对于饴我们非常清楚,是一种麦芽糖。因此“豆饴”与豆浆无关,可能是介于固体与液体之间的食品。“豆饧”应该类似之,何况 *** “饧”需要“煮米消烂”,无论是在米中添加豆屑还是直接煮豆“消烂”,均不是研磨的豆浆。高启安曾根据敦煌文书认为豆饴是“将豆屑 *** 成‘怡怡然’的物质”,并且指出他所认为的“早期豆腐”并不是用豆浆制成。
豆腐的起源问题往往与豆浆牵扯在一起,袁翰青认为,豆腐的 *** 与豆浆有天然的关系,必须先制出豆浆方能点豆腐。此后诸多研究者均从豆浆论证豆腐的起源,或是将汉代已有豆腐作为豆浆已经出现的证据。这种观点以今日的 *** 工艺来反推古人,下文将指出,早期 *** 豆腐未必使用豆浆,煮烂的“豆粥”同样可以过滤后制豆腐。如果我们将豆浆与豆腐之间的固有关联拆开,豆浆与豆腐的起源都是具有争议的问题,那么既不能用豆浆出现来作为豆腐发明的前提,也不能用具有争议的豆腐起源观点,来证明豆浆早已有之。
二、战国秦汉出土“湿磨”献疑
从出土文物考察豆腐、豆浆的起源,以往学者注意到战国秦汉时期出土的许多石转磨均有利于研磨流质物料,因此最有可能用来研磨大豆。此说最早见于卢兆荫等人的研究,该文提出满城汉墓中石转磨系湿磨,主要用途是将农作物磨制成流质,如麦浆、米浆、豆浆等。此后相似结构的转磨多有出土,相关研究者结合农作物种植分布提出这种湿磨最有利于大豆,甚至认为早期的转磨并非用于磨粉,而主要是磨大豆。其中赵梦薇的研究充分吸收了前人意见,对这一观点做了 *** 总结和探讨。倘若此说成立,那么豆浆进入日常生活最迟至汉代也已完成。
下节对文献的详细梳理将指出,中古时期并不存在饮用豆浆的习惯,因此上述观点与文献记载存在明显的抵牾。如果汉代时研磨豆浆已非常常见,不可能在整个中古时期均无食用豆浆的记载,曹植、石崇等没有必要 *** 如此复杂的豆粥,医学文献中的大豆加工方式亦会充分利用研磨。近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重新讨论,提出转磨的起源与发展得益于小麦广泛种植的推动,该文谈到卫斯、赵梦薇的相关研究,却没有对大豆在转磨发展中的意义做出回应。很明显,依据石转磨形制来断定豆浆已进入到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下面以赵梦薇文中的证据为主,对该问题提出笔者的浅薄看法。
赵文完善了周昕先生的观点,指出转磨最早被用于磨粉,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更适于研磨大豆。转磨的出现一定是与加工小麦有关,因为中国食用大豆的历史非常悠久,长期以来均不需要研磨。同样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抛开“豆浆早已有之”这种毫无根据的前提,汉代人是否会去研磨大豆却很值得怀疑。赵梦薇提出西汉中期之前的转磨以“湿磨”为主,此后逐渐变为旱磨,这种认识基于许多出土石磨的承盘带有流口和漏孔,认为研磨的粉“显然不好从流口排出”。但张凤认为承接器为浅盘的应为磨制面粉的旱磨,为漏斗的才是更利于流质的湿磨。事实上,带有流口或漏孔的浅盘式与漏斗式的原理一致,都是使研磨得到的物质能够集中于一个小口流出,便于用其他容器承接。“承盘”在使用时可以人为将面粉汇聚于流口和漏孔,并非不能研磨面粉。简而言之,加工流质必须使用漏斗或承盘,但是使用漏斗与承盘的石磨未必一定用于加工流质,汉代是转磨运用的早期阶段,存在各种不合理之处亦属正常,不能过度以“技术理 *** ”分析之。同时赵文中指出“早期鲁南徐州地区的旋转石磨以湿磨为主,干磨仅有一例”,这更能说明此时并未有旱磨、湿磨之分,这种类似于今日湿磨的设计是早期石磨的主流形态,其主要用途毫无疑问还是研磨小麦或粟黍。西汉中期以后“旱磨”的大幅增加,即表明转磨在向适宜磨麦的方向演化。
另外,周昕先生关注到上扇出现的两个半圆形,认为一个用来加水,一个用来加物料,或均加含水的物料。这种推测似乎没有道理,只有一个口同样可以放入带水的物料,并不影响研磨。今日湿磨与干磨均有两孔入料。上引傅文彬、赵志军认为这两个入料口是今石磨中常见的“快慢眼”,提出“双磨眼的结构则很可能就是为了精加工小麦而设计的”,此说有一定可能 *** 。但快慢眼需要两孔大小不同,方能体现“快慢”,满城汉墓等地出土的“横梁式”入料口却是两孔等大。无论如何,这一特征不能判断是湿磨或旱磨。至于上引大多数学者都以汉代已有豆腐作为证据,表明研磨豆浆是日常生活必备工艺,此说的前提即存在较大争议,自不能为探讨转磨用途提供参考。
同样,早期转磨结构确实有利于磨制流食,我们也不可能认为转磨全部用来磨粉,这种推断过于武断。但不能据此说明一定会磨制大豆,正如卢兆荫等提出满城汉墓可能用于磨制 “麦浆、米浆、豆浆”,该表述说明其认为麦浆的可能 *** 更大,“麦浆”一词的出现远早于“豆浆”,《抱朴子·内篇》记载其服食 *** :“以麦浆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饵之,亦可以龙膏炼之。”《肘后备急方》也有关于麦汁的记载:“苦参三两,龙胆一合,末,牛胆丸如梧子,以生麦汁服五丸,日三服。”其中“生麦汁”无疑是通过研磨或捣碎麦制成的。文献材料表明研磨麦浆麦汁的习惯要远早于豆浆或豆汁,这是由于食用大豆自有长期以来的传统,豆粥、豆羹、豆饭等食物深入人心,且在主粮构成中未占有主要地位;而小麦作为域外传入食品,必须探索其食用 *** ,干磨成粉或湿磨成浆本身只是同时探索的两种方向。同时,对于出土转磨的生物分析表明,豆科植物淀粉粒在汉代转磨中含量很少,实验所用的四方转磨中均不超过4%,同时从淀粉粒来分析应当为绿豆、豌豆、豇豆等植物。充分证明此时研磨大豆食用极少。这些绿豆、豌豆等比大豆容易食用,将其研磨更有可能是磨粉,用以 *** 饼食或类似于今日“粉条”之物。
因此,在没有磨制大豆的确切证据下,不宜以出土的所谓“湿磨”证明豆浆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排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人曾经加水磨制大豆,但是磨制豆浆长期以来并未成为一种食品,更没有成为日常生活常见食品。同时,这些类似于今天“湿磨”的发现,表明古人早已具备研磨豆浆的技术能力,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技术应用颇有意义,下文还将述及。
三、汉唐之间疑似豆浆之物辨析
既往研究针对“豆浆”所提出的文献与考古证据,具有诸多可商问题,说服力有限。对于豆浆起源与推广的研究,应当充分辨析文献,详细梳理豆浆相关食品的记载,探寻豆浆 *** 相关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脉络。
前文中提到了“豆屑”物,如果豆屑是研磨豆浆剩下的豆渣,那么亦可证明豆浆的存在。关于豆屑的文献非常多,如“以大豆屑饼之”,“生大豆屑,酒和服方寸匕”。唐代“豆屑”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提到大豆屑,注明需要“熬”。《新唐书》记载:“黄巢未入京师时,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谓之‘黄贼 *** 贼’。”这豆屑既可以做饼和蒸食,又需要“熬”制使用,豆渣做不到这些,只能是今天的“豆粉”“豆面”之类,并没有脱去蛋白质。对此结论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清人曾记载一个断案故事:“黄洽中为乌程令,有豆商、米商共争一斛,洽中曰:‘两家构争,皆斛罪也。’叱杖之,斛破,豆屑出焉,乃罪米商。”这里的豆屑显然不是磨制的豆渣,而是大豆的粉末,清代豆浆已风行,此时“豆屑”仍未有“豆渣”之意。
同时古人早已有大豆加水煮熟的食用 *** ,即为“豆羹”。著名的《七步诗》详细记述了“豆羹”的 *** 过程:“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该诗见于《世说新语》,无论是否为曹植所作,均可 ***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对于“豆羹”的理解,可见这种豆羹是将大豆直接放在“釜”中煮烂而成的。从“羹”字本义可知“豆羹”应当是不过滤的,该诗下句“漉菽以为汁”,“汁”或许与“羹”对立为两种食物,但也反映出此时在上层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过滤大豆直接饮用“豆汁”的做法。无论过滤与否,“豆羹”是直接煮大豆的食品,并非豆浆。
这里的“豆汁”在《齐民要术》中有详细介绍:“更煮豆取浓汁,并秫米女曲五升;盐五升,合此豉中。以豆汁洒溲之,令调。以手抟,令汁出指间,以此为度。”与《七步诗》中为同一物,均为煮豆后获得的汁。葛洪《肘后备急方》亦有饮用“豆汁”的 *** :“小豆一斛,煮令极烂,得四五斗汁,温以渍膝已下,日二为之,数日消尽。若已入腹者,不复渍,但煮小豆食之,莫杂吃饭及鱼盐。又专饮小豆汁。无小豆,大豆亦可用。”这里表现服用小豆亦用煮。同书亦有“大豆汁”制取 *** :“大豆一斗,熟煮,漉饮汁及食豆,不过数度必愈,小豆尤佳……大豆一升,以水五升煮二升,去豆,纳酒八升更煮九升,分三四服。”此类用法非常多,均为直接煮烂大豆,然后过滤掉大豆服用“豆汁”。“熟煮”的过程中,部分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能够脱离大豆溶于水中,这样得到的“豆汁”,从其成分来看与今日的豆浆接近。但两者 *** 工艺不同:一为煮食,一为研磨。
《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这是中古时期唯一一次出现“豆糜”这个词,该文字之后的注文中谈到:“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户。其法先以杨枝 *** 于左右门上,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糕糜 *** 箸而祭之。”这里似乎将“豆糜”分开解释为“豆粥”“糕糜”。《荆楚岁时记》本身就是记载风土习俗的书籍,作者将豆粥称之为“豆糜”,可能是地方 *** 的称呼,因此非常少见。由于“糜”字的含义即是粥,所以无论是“豆糜”还是“豆粥糕糜”,相关研究大多将其视为“豆粥”。豆粥是直接将完整大豆放入水中煮熟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可以佐证:“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石崇想喝豆粥很快就能喝到,是因为他的下人提前将其煮熟再做成“豆末”,这里“豆至难煮”表明一般情形之下的豆粥,正是直接将大豆置于水中煮熟,因其体积较大而需要较多时间。
综上所述,中古时期有许多疑似为豆浆的食品,经过分析史料能够得出,豆饧、豆饴、豆羹、豆汁、豆糜与豆粥,都与今日所饮之豆浆有明显差别。
孙思邈记载:“捣赤小豆五合,水和,取汁饮之一合良,滓涂五心。”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是“捣豆”中就加入水,还是先干磨,再加水泡出浆?如果是前者,那就是用赤小豆制成了豆浆;但从语序来分析,更有可能是先干磨再泡出浆,与此后的豆浆不同。相对于葛洪煮烂赤小豆的 *** ,这里已改为研磨后饮用,只是没有加热。该文后也涉及大豆加工:“浓煮大豆汁涂之良,瘥亦无瘢痕。”却与葛洪服用大豆的方式类似,也是直接“煮豆取汁”。孙思邈为何对于大豆和赤小豆的处理 *** 不同?一方面大豆比赤小豆体积要大,加工会更有难度;另一方面,这表明中古时期的人们早已注意到大豆中物质的重要价值,但并没有研磨大豆饮用的习惯,连医家用 *** 都尽量不采用研磨 *** 处理大豆。
《证类本草》引《唐本草》中有:“中者,研生绿豆汁,饮一、二升解之。”这一记载较为明确,就是生的绿豆浆,其工艺与豆浆已经非常接近。但这里是生食,又使用绿豆,由于中医临床实践中对于 *** 物的处理有一套独特理念,因而也不能据此认定已将豆浆作为日常食品。不过,我们能够从葛洪以来处理大小豆 *** 的变化,注意到研磨技术逐渐被 *** 物加工吸收借鉴。
从“豆屑”的 *** 可以得知,古人早已具备研磨大豆的技术能力,能够将其磨成“豆屑”,便能够将其磨成豆浆与豆渣。同时,饮用“豆汁”说明此时已具备过滤与煮食的技术能力。这表明古人已经具备了 *** 豆浆的全部技术基础,也是许多学者认为“豆浆早已有之”的主要依据。但文献反映出,人们一直坚持使用“煮烂”的 *** 获取其中的营养物质,并没有诞生豆浆。这一点王利华在研究豆腐起源时已经指出:“我们发现中古以前国人解渴主要是饮浆,在那时的文献之中见过用不同材料做的许多名目的‘浆’,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一条材料反映汉唐之间人们磨豆煮浆饮用。”虽然只是一种初步判断,未展开深入探讨,但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磨豆、煮浆、饮汁三种做法,却的确没有发现“磨豆煮浆饮汁”共同发生的饮食习惯。豆浆成为饮品并广为人知,还需要到中古之后的宋元时期。
四、关于豆浆的明确记载
事实上,“豆浆”此物的出现与其成为广泛食用的饮品,应当是两个阶段。前文谈到,古人早已具备制取技术,因此饮用豆浆成为生活习惯只是时间问题,但需要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其推广开来,最终实现这一结果已经迟至元代。
《外台秘要》曾引《经心录》中“豆浆粥”的做法:“右二味作散,和鸡子七枚,令熟并 *** 作丸,煮赤豆作浆粥,服三十丸,日三服。若渴,饮豆浆粥。”这里“煮赤豆作浆粥”表明应当是直接煮烂赤豆,未经研磨。此后,明清之际的谈迁详细记载了北京地区“豆浆粥”的做法:“都肆中以豆屑杂少米煮之如薄糜,晨哺一二瓯,最补元神。”这里使用豆屑,可能是因为大豆直接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煮烂,用豆屑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从唐代至清代,“豆浆粥”的概念可能发生变化,但从史料分析都不是将豆浆加入粥中,而是直接煮豆使其中的蛋白质等物质析出。唐末《四時纂要》谈到:“吐甚者,即研小绿豆浆服之,即止。”缪启愉先生如此点读,但此处是“即研小绿豆,浆服之”还是“即研小绿豆浆,服之”,两种理解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很可能获得干的豆粉,也可能获得糊状的“豆泥”,但缺少过滤过程,直接加水服食。如果是后一种理解,即饮用过滤后得到的生豆浆。无论作何解释,均与后世的“豆浆”有一定差别。
宋代豆腐已经广泛出现于食谱之中,陶穀《清异录》中也有对豆腐的明确记载。袁翰青等学者认为豆腐是在食用研磨豆浆后发明的,按此思路,宋代有豆浆已不证自明,但史料中并没有出现饮用豆浆的记载。《证类本草》引《太平圣惠方》云:“以桑柴灰热汤淋取汁洗头面(以大豆水研取浆,解泽灰味,弥佳)。”这里是将大豆加水研磨,然后过滤得到“浆”,记载十分明确,与今日生豆浆并无差别。但其用途是冲洗脸上的灰,并不饮用。同时,《本草衍义》中描述大豆“又可硙为腐食之”,“硙”即研磨,应是磨豆浆做豆腐,仅介绍了大豆可以 *** 豆腐,没有谈到豆浆。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日常生活中并不将豆浆作为食品,而只是豆腐 *** 过程中的半成品。高启安也已提出,豆腐未必是豆浆制成,可以用豆粉。煮烂大豆后过滤得到的“豆汁”,由于其成分与豆浆近似,亦可作为 *** 豆腐的原料。因此,尽管此时豆腐已经明确出现,但仍不能以豆腐的出现作为豆浆成为食品的证据。
元 *** 始豆浆成为广为人知的食物,能够看到较多确切记载。刘时中有曲《端正好》,其中写道:“或是捶麻柘稠调豆浆,或是煮麦麸稀和细糠。他每早合掌擎拳谢上苍。一个个黄如经纸,一个个瘦似豺狼,填街卧巷。”这里应该是将麻、柘两种植物的叶子捶打后混入豆浆之中,由于该曲是为反映饥荒情景,豆浆也不可能过滤,因此是“稠调豆浆”。此外《世医得效方》记载:“上用桑枝灰一斗,热汤淋取汁,洗头面。次用大豆及绿豆浆添熟水,三日一浴,一日一洗面。”此是前引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水研取浆”的 *** ,但这里已经简化为“大豆及绿豆浆”,可知“豆浆”之含义已为人所共知,不需要再多加解释,说明豆浆成为日常生活常见食品。此外,《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一件关于农夫“司大”的故事,其中有一细节:“司无以为养生计,即所偿钱为豆乳酿酒,货卖以给食。久之,不复乏绝,更自有余。”宋代以后,豆腐和豆浆都会被称为豆乳,能够酿酒的显然不会是豆腐,而是豆浆。这里还揭示出此时已有人卖豆浆为生,表明豆浆在社会上得到广泛食用。《名山藏》记载明 *** 国大将汤和,在参加红巾军之前,也是以卖豆浆为生。
据此,元代豆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中,社会下层未必有能力经常饮用,但已对这种食品不陌生,许多人以卖豆浆为生。食品的推广需要一定时间,豆浆很可能在南宋中后期已成为食物,到元代普遍推行并进入到文人的笔下,将豆浆开始食用确定在宋元时期较为合适。
这里有几条记载需要作出辨析。一是《疮疡经验全书》中谈到涂抹生豆浆:“右为末,生豆浆调匀,搽四向空, *** 毒气时用余浆润之,以助 *** 力。”该书一直署名宋代名医窦汉卿,相关研究认为该书应当是明代的窦梦麟以家传善本及 *** 窦楠的验方为基础,校勘而成,窦梦麟并非窦汉卿的直系后人,其家传善本最早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的窦良茂。由此从知识来源的角度看,这一豆浆用法应为明代形成。二是《李师师外传》中写李师师婴儿时只能吃“菽浆”:“寅妻既产女而卒,寅以菽浆代乳乳之,得不死。”菽浆即为豆浆。李裕民列举了书中诸多不合宋朝事实之处,指出应为清初明朝遗民所作。“菽浆”一词在文献中非常少见,明代中后期之前从未出现,也为判定此书并非宋人作品提供了新的证据。三是《大金国志》中常被引用来描述女真人早期生活方式的一段话:“饮食甚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嗜酒,好杀。酿糜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 *** 。”其中“以豆为浆”的记载,一直被理解为金人爱饮豆浆,甚至有学者提出在金朝建立后 *** 开始模仿女真人的生活习惯,喝豆浆成为一时之尚。同时,《三朝北盟会编》中亦收录一段类似叙述:“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许涵度校正时在其后曾注“删以半至此二十四字”,可知“以豆为酱”四字应属原文内容,并非许氏擅改。过去有关金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可能由于史料太过缺少,因此研究者大多选择两者均采信,金人既用豆制豆浆,也用来做酱。有学者曾注意到这一问题:“这里的‘酱’,有版本作浆,但似应作‘酱’。”仅对其做了推测,未及展开。从内容上来看,两种叙述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酿酒、半生米饭、渍狗血等要素具在,只是排列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两种记载中有一种为误,两说不可并存。《三朝北盟会编》成书更早,《大金国志》中这段叙述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三朝北盟会编》中的相关内容,只是在编纂、传写或是刊刻 *** 现了讹误,误“酱”为“浆”。故而不能以此认定女真人已有服用豆浆的风俗,南方后来出现的饮用豆浆习惯,也不能视作受到少数民族影响。
五、余论:饮用豆浆与“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
实物与文字记载两方面均显示,古人早已拥有制造豆浆的技术能力。研磨豆浆并煮食的技术基础并不复杂,最晚在汉魏时期就能完全实现。那为什么豆浆一直到宋元时期才成为日常饮食呢?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既能更新我们对技术基础与发明出现两者关系的认知,又能进一步看到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之间的关系。
豆浆,如果我们将其作为饮食中的一项技术发明,那么它的 *** 工艺应当由几项关键技术构成:技术一是研磨大豆,技术二是将残渣与液体分离开,技术三是煮食。事实上,缺少任意一项都使其与食用豆浆有明显的距离,上文已经述及,这三项技术均有较早的明确记载,但“豆浆”这一发明的完整出现却要迟至宋元时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往往认为当技术基础成熟之时,即可作为新发明出现之日,此前对豆腐与豆浆的研究均存在这种问题。已有许多研究在思考这一现象,如王利华指出:“科学技术史上的众多事实表明:将若干单项技术联结起来,集成为另外一套新的彼此配套的复合技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发明创新过程,常常需要经过长期摸索才能实现。”本文的结论即可证明,技术基础与发明出现不具有明确的关系,即使在技术基础全部成熟并得到应用的情况下,依然有可能相隔较长时间才出现技术创新或发明。
同时,宋代已经出现豆腐,史料中有不少磨豆制豆腐的记载。未点卤之前的豆腐就是豆浆,可以认为技术发明已经出现,但人们一开始并没有将其视作一种饮料,更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食品。于是乎出现了日常生活中食用豆腐早于饮用豆浆几百年的历史现象,这与我们既往的认知颇为不洽,一定程度上也 *** 了豆腐起源研究的开展。同时,研磨大豆的 *** 一直留存于医疗实践中,长期以来未进入到日常饮食之中,民众还是食用煮豆粥。豆浆之后成为饮品,这项技术恐怕还是从豆腐 *** 工艺中迁移而来。这些现象揭示出技术创新与技术的推广和转移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实用技术的推广与普及,需要技术之外的社会因素提供力量。
在煮豆粥的时代,其实人们已经注意到,煮烂大豆得到的“豆汁”非常有价值,可将其用于治疗疾病、作为优质饮品。如果先研磨再过滤,显然是一种效率更高的技术,但是普通民众和达官显贵均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古代的下层民众食用豆制品时是不可能放弃豆渣去享受豆浆的,为了获取豆浆而得到副产品豆渣,是一种本末倒置,直接煮食大豆对农事繁忙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更合算的方式。直到几十年前的农村,很多家庭研磨豆浆是不过滤的,连同豆渣一起配上青菜作为主食,这在很多地方被称为“懒豆腐”,其实也符合国人节俭的传统美德,一定要物尽其用。对于上层社会来说,石崇是很好的例子,煮烂大豆无非是消耗更多燃料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去关心“豆汁”是煮烂还是磨烂的。宋元时期,城市、市镇人口的增加与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豆浆消费的土壤,尤其是豆浆开始作为商品 *** 。在一定规模的经营之下,研磨豆浆显然要比煮烂豆粥成本更低,也能卖出更高的价钱。对于市民来说,一方面远离农业生产,不需要自己从事研磨,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豆浆成为一项日常生活饮食得到推广,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原因,包括口感、饮食结构、研磨技术等方面,但这一因素最为主要,豆浆可能是作为豆粥的替代品首先受到欢迎。
李昕升提出“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的观点,认为国人对于外来作物的接受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嵌入到中国传统的种植 *** 和饮食文化之中。种植 *** 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经济问题,外来作物不能融入原有耕作体系,将导致实际收益的下降。这一判断主要针对外来作物提出,实际上本土食品进入到日常生活,也要考虑到原有饮食结构。大豆是本土传统作物,食用豆制品并不涉及种植 *** 问题。但豆浆不能得到推广,主要是 *** 工艺带来的经济成本 *** ,在没有庞大消费群体和高效商品交换之前,难以成为日常饮食。相比之下,豆腐能够早于豆浆普及,是因为豆腐是一种素菜,尽管比豆浆的成本还要高一些,但作为菜而不是主食,则又是较为廉价的。其融入原有的饮食结构是比较容易的,各阶层人民都乐于获得这种美味又相对便宜的食品作为菜肴,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主要是想尝试美味,下层人民则为了补充食材的稀缺,因之宋代以后的文艺作品中食用豆腐常被视作清贫的象征。
因此,豆浆 *** 工艺的形成与推广,都不是仅仅由科学技术本身决定的。任何一项技术创新的出现与推广,要到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并产生相应的需求时才能实现。我们将科学技术史分为“内史”与“外史”,梳理内史发展能够看出科学技术自身演进的脉络,但若是不关注社会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有些现象就难以解释。
最后,揭示豆浆的社会起源对于推进豆腐起源的研究也具有一定价值。前文述及,许多学者站在今天角度上,认为熬制豆浆饮用是豆腐发明的前提,后来者研究豆腐循此思路,陈文华与孙机等人争论的核心为画像石上是不是磨,应克荣等人论证刘安发明豆腐也十分重视石磨。豆腐早于豆浆被食用,表明早期的豆腐未必是豆浆所 *** ,有可能如高启安所推测是豆粉豆面制取,但更有可能是煮豆粥之后对固体成分过滤,再制成豆腐。例如苏轼诗中“煮豆作乳脂为酥”,这里“煮豆作乳”表明是通过煮这个过程获得的“乳”,因而并非研磨好的豆浆,而是煮烂大豆后形成的豆粥,再过滤为“脂”,最终加工成豆腐。豆粥在中古时代十分常见,用豆粉煮汁再过滤则较少。
文章来源于《农业考古》2022年第4期
原料都是豆子,“豆汁”和“豆浆”区别在哪,为啥走不出北京?原料都是豆子,“豆汁”和“豆浆”区别在哪,为啥走不出北京?
导语:到北京旅行,登长城、游故宫是外地朋友必备的项目之一,而有些勇敢的朋友,还会尝试挑战一种“黑暗料理”——豆汁,不过很多人还是以失败告终,有的人喝了一小口之后,就默默放下来碗,不想再喝第二口了。
多数人对于豆汁的感觉,总结起来,大概就是这几个词语——“酸腐味道”、“酸酸馊馊”、“一股泔水味”,都是一些“差评”的词语,所以豆汁才一直走不出北京。不过,对于北京人来说,他们就好这一口,清晨来一碗豆汁,就是美好一天的开始。
早在辽宋时期,豆汁就成为了民间大众化的美食,从清朝开始,豆汁就在北京流行起来。在乾隆 *** ,豆汁更是成为了宫廷的御膳。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乾隆皇帝招募了多名豆汁工匠进驻御膳房,并且召集一众大臣品尝豆汁,结果大家喝了之后,纷纷拍手称赞。
“豆汁”和“豆浆”区别在哪?
对于南方人来说,可没有豆汁这东西,只有豆浆这一食物。于是人们就有这么一个疑问,豆汁和豆浆是不是同一种东西?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事实上,虽然它们都是以豆子为原料,但却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食物。豆浆是用黄豆加水研磨之后得到的浆液,而豆汁则是用绿豆作为原料,把粉丝的下脚料发酵以后,放入大锅里煮一煮,随后再过滤,这就是豆汁了。
因为有了发酵的过程,所以豆汁总是散发出浓郁的酸腐味道,像是摆放了好几天的食物。虽然外地朋友对于豆汁都避而远之,但是老北京可是豆汁的“狂热粉丝”,每天去豆汁店打卡,已经成为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如果喝习惯了豆汁,其实这个玩意还是挺上瘾了,就像是喝水一样,每天都要喝。
喝豆汁有什么讲究?
之前认识了一个北京的朋友,是一个老北京,他说喝豆汁一定要配咸菜丝,咸菜丝必须要切成丝儿,这样才是最地道的品尝方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喝豆汁配焦圈,所以大众才认为焦圈才是最地道的吃法。实际上,北京人吃烧饼时才会夹着焦圈。
其次,喝豆汁不用勺子,一定要用手托着碗底,嘴唇贴着碗边,碗慢悠悠地在嘴边转着圈儿,这种喝豆汁的方式,在北京话里叫做“吸溜儿”,这一词语,对于喝豆汁的动作描写,形容得既生动又形象。
不要看豆汁其貌不扬,它的营养价值可是非常高,其中富含蛋白质、维生素C、粗纤维和糖分。只不过现在地道的豆汁店为数不多,正宗的豆汁更是难以寻觅。
你喜欢喝豆汁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分享自己的感想和想法。今天大熊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觉得文章有用的话,请分享转发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我是大熊饼干不加糖,每天分享给大家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喜欢我就点个关注吧,谢谢!
豆浆和豆汁有什么区别?豆汁和豆浆的区别在于:
·原料不同。虽然都是豆制品,但豆汁使用绿豆,而豆浆则使用黄豆。
· *** 方式不同。豆浆的 *** 相对简单,只需经过浸泡、磨碎、煮沸和过滤即可完成。而豆汁需要发酵。
·颜色不同。豆汁和豆浆在颜色上也有所不同。豆浆呈奶 *** ,颜色干净清新;而豆汁颜色更深,通常偏绿色或灰色,与绿豆汤相似。
·口味不同。豆汁和豆浆的口感差异较大。豆浆口感香醇,豆香味浓郁,回味悠长;而豆汁入口酸味涩味,带有馊味,味道刺鼻。豆汁的味道备受争议,许多人无法接受。
关注我,为你解决日常问题。
中国古代饮用豆浆的起源与推广【摘要】饮用豆浆从宋 *** 始出现,元代成为日常饮食。在此之前出现的豆饬、豆饴、豆羹、豆汁、豆粥、豆糜等物均非豆浆,中古时期并没有饮用豆浆的习惯。考古出土的早期石转磨在结构上类似湿磨,但并不能证明其用途是磨制豆浆。豆浆成为食品并不在豆腐发明之前,早期豆腐可能并不是由豆浆 *** 。研磨豆浆的技术条件早已具备,但饮用豆浆开始于宋元时期城市经济繁荣之后。体现出技术基础满足并不一定出现技术创新,技术发明的推广更需要考虑技术之外的社会因素,中国古代“超稳定饮食结构” *** 了豆浆的发明、推广,这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视角去观察并思考古代科技。
豆浆,又称豆乳,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种美食。大豆研磨之后再过滤煮熟,就制成了我们日常饮用的豆浆。古人亦能享受豆浆的美味,但我国先民究竟从何时开始将豆浆作为日常食品,该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梳理豆浆的起源与发展,不仅可以明晰豆浆的历史,同样有助于认识豆粥、豆腐等食品的产生发展。既往研究中涉及豆浆起源的不可谓不多,提出了许多观点与证据,但多有可讨论之处。本文首先对既往观点作一辨析,在此基础上重新检核材料,分析豆浆及其相关食品的名与实,探讨豆浆从技术基础的形成到推广为日常饮食这一曲折复杂的历程,并尝试由此揭示古代科技发明与饮食文化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
一、既往豆浆起源研究的辨析
目前所见的研究,几乎全部认为至少在汉代豆浆已经出现。其论据可分为三种:一是文献中的“豆浆”记载;二是由豆腐的出现反推豆浆,三是考古出土的石转磨利于磨制豆浆。本节先分析前两种证据。
林乃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提出《盐铁论》中的“豆饧”,应当是一种甜豆浆或豆腐脑。原文“豆赐”最早由卢文弨校为“豆饧”,各家对其观点不一,《盐铁论校注》的校勘记中列举“锡”“饧”“肠”各种观点均有,是否应为“豆饧”不为确论。王佩诤认为其应为“豆豉”之误。此外,陈直从对仗的角度提出“胹羔豆饧”应为一动词领三名词,“羔为糕字之省文,豆作粉饵,饧为饴糖,属于小食类,皆烂熟以食也”。还反驳了王佩诤的观点:“豆豉”不须研磨;“粉饵”则是豆粉制成的糕点,与豆浆无干。以上诸说各有其道理,但均为历代注家对“豆赐”含义的猜测,显然不能作为证明豆浆或豆腐存在的有力证据。
即使“豆饧”的确存在,此物也不会必定是豆浆或者豆腐。《释名》曰:“饧,洋也。煮米消烂,洋洋然也……饴,小弱于饧,形怡怡然也。”两物密切相关,因此“豆饧”与“豆饴”应当比较接近。《太平御览》引《苍颉解诂》谈道:“饴中着豆屑也。”《玉篇》又曰:“饴,和豆也。”可知所谓“豆饴”是“饴”添加豆屑之物。对于饴我们非常清楚,是一种麦芽糖。因此“豆饴”与豆浆无关,可能是介于固体与液体之间的食品。“豆饧”应该类似之,何况 *** “饧”需要“煮米消烂”,无论是在米中添加豆屑还是直接煮豆“消烂”,均不是研磨的豆浆。高启安曾根据敦煌文书认为豆饴是“将豆屑 *** 成‘怡怡然’的物质”,并且指出他所认为的“早期豆腐”并不是用豆浆制成。
豆腐的起源问题往往与豆浆牵扯在一起,袁翰青认为,豆腐的 *** 与豆浆有天然的关系,必须先制出豆浆方能点豆腐。此后诸多研究者均从豆浆论证豆腐的起源,或是将汉代已有豆腐作为豆浆已经出现的证据。这种观点以今日的 *** 工艺来反推古人,下文将指出,早期 *** 豆腐未必使用豆浆,煮烂的“豆粥”同样可以过滤后制豆腐。如果我们将豆浆与豆腐之间的固有关联拆开,豆浆与豆腐的起源都是具有争议的问题,那么既不能用豆浆出现来作为豆腐发明的前提,也不能用具有争议的豆腐起源观点,来证明豆浆早已有之。
二、战国秦汉出土“湿磨”献疑
从出土文物考察豆腐、豆浆的起源,以往学者注意到战国秦汉时期出土的许多石转磨均有利于研磨流质物料,因此最有可能用来研磨大豆。此说最早见于卢兆荫等人的研究,该文提出满城汉墓中石转磨系湿磨,主要用途是将农作物磨制成流质,如麦浆、米浆、豆浆等。此后相似结构的转磨多有出土,相关研究者结合农作物种植分布提出这种湿磨最有利于大豆,甚至认为早期的转磨并非用于磨粉,而主要是磨大豆。其中赵梦薇的研究充分吸收了前人意见,对这一观点做了 *** 总结和探讨。倘若此说成立,那么豆浆进入日常生活最迟至汉代也已完成。
下节对文献的详细梳理将指出,中古时期并不存在饮用豆浆的习惯,因此上述观点与文献记载存在明显的抵牾。如果汉代时研磨豆浆已非常常见,不可能在整个中古时期均无食用豆浆的记载,曹植、石崇等没有必要 *** 如此复杂的豆粥,医学文献中的大豆加工方式亦会充分利用研磨。近期有学者对这一问题重新讨论,提出转磨的起源与发展得益于小麦广泛种植的推动,该文谈到卫斯、赵梦薇的相关研究,却没有对大豆在转磨发展中的意义做出回应。很明显,依据石转磨形制来断定豆浆已进入到日常生活中,这种观点是存在问题的。下面以赵梦薇文中的证据为主,对该问题提出笔者的浅薄看法。
赵文完善了周昕先生的观点,指出转磨最早被用于磨粉,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更适于研磨大豆。转磨的出现一定是与加工小麦有关,因为中国食用大豆的历史非常悠久,长期以来均不需要研磨。同样基于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抛开“豆浆早已有之”这种毫无根据的前提,汉代人是否会去研磨大豆却很值得怀疑。赵梦薇提出西汉中期之前的转磨以“湿磨”为主,此后逐渐变为旱磨,这种认识基于许多出土石磨的承盘带有流口和漏孔,认为研磨的粉“显然不好从流口排出”。但张凤认为承接器为浅盘的应为磨制面粉的旱磨,为漏斗的才是更利于流质的湿磨。
事实上,带有流口或漏孔的浅盘式与漏斗式的原理一致,都是使研磨得到的物质能够集中于一个小口流出,便于用其他容器承接。“承盘”在使用时可以人为将面粉汇聚于流口和漏孔,并非不能研磨面粉。简而言之,加工流质必须使用漏斗或承盘,但是使用漏斗与承盘的石磨未必一定用于加工流质,汉代是转磨运用的早期阶段,存在各种不合理之处亦属正常,不能过度以“技术理 *** ”分析之。同时赵文中指出“早期鲁南徐州地区的旋转石磨以湿磨为主,干磨仅有一例”,这更能说明此时并未有旱磨、湿磨之分,这种类似于今日湿磨的设计是早期石磨的主流形态,其主要用途毫无疑问还是研磨小麦或粟黍。西汉中期以后“旱磨”的大幅增加,即表明转磨在向适宜磨麦的方向演化。
另外,周昕先生关注到上扇出现的两个半圆形,认为一个用来加水,一个用来加物料,或均加含水的物料。这种推测似乎没有道理,只有一个口同样可以放入带水的物料,并不影响研磨。今日湿磨与干磨均有两孔入料。上引傅文彬、赵志军认为这两个入料口是今石磨中常见的“快慢眼”,提出“双磨眼的结构则很可能就是为了精加工小麦而设计的”,此说有一定可能 *** 。但快慢眼需要两孔大小不同,方能体现“快慢”,满城汉墓等地出土的“横梁式”入料口却是两孔等大。无论如何,这一特征不能判断是湿磨或旱磨。至于上引大多数学者都以汉代已有豆腐作为证据,表明研磨豆浆是日常生活必备工艺,此说的前提即存在较大争议,自不能为探讨转磨用途提供参考。
同样,早期转磨结构确实有利于磨制流食,我们也不可能认为转磨全部用来磨粉,这种推断过于武断。但不能据此说明一定会磨制大豆,正如卢兆荫等提出满城汉墓可能用于磨制 “麦浆、米浆、豆浆”,该表述说明其认为麦浆的可能 *** 更大,“麦浆”一词的出现远早于“豆浆”,《抱朴子·内篇》记载其服食 *** :“以麦浆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饵之,亦可以龙膏炼之。”《肘后备急方》也有关于麦汁的记载:“苦参三两,龙胆一合,末,牛胆丸如梧子,以生麦汁服五丸,日三服。”
其中“生麦汁”无疑是通过研磨或捣碎麦制成的。文献材料表明研磨麦浆麦汁的习惯要远早于豆浆或豆汁,这是由于食用大豆自有长期以来的传统,豆粥、豆羹、豆饭等食物深入人心,且在主粮构成中未占有主要地位;而小麦作为域外传入食品,必须探索其食用 *** ,干磨成粉或湿磨成浆本身只是同时探索的两种方向。同时,对于出土转磨的生物分析表明,豆科植物淀粉粒在汉代转磨中含量很少,实验所用的四方转磨中均不超过4%,同时从淀粉粒来分析应当为绿豆、豌豆、豇豆等植物。充分证明此时研磨大豆食用极少。这些绿豆、豌豆等比大豆容易食用,将其研磨更有可能是磨粉,用以 *** 饼食或类似于今日“粉条”之物。
因此,在没有磨制大豆的确切证据下,不宜以出土的所谓“湿磨”证明豆浆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排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人曾经加水磨制大豆,但是磨制豆浆长期以来并未成为一种食品,更没有成为日常生活常见食品。同时,这些类似于今天“湿磨”的发现,表明古人早已具备研磨豆浆的技术能力,这一现象对于我们理解古代技术应用颇有意义,下文还将述及。
三、汉唐之间疑似豆浆之物辨析
既往研究针对“豆浆”所提出的文献与考古证据,具有诸多可商问题,说服力有限。对于豆浆起源与推广的研究,应当充分辨析文献,详细梳理豆浆相关食品的记载,探寻豆浆 *** 相关技术发展与应用的脉络。
前文中提到了“豆屑”物,如果豆屑是研磨豆浆剩下的豆渣,那么亦可证明豆浆的存在。关于豆屑的文献非常多,如“以大豆屑饼之”,“生大豆屑,酒和服方寸匕”。唐代“豆屑”的记载开始大量出现,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提到大豆屑,注明需要“熬”。《新唐书》记载:“黄巢未入京师时,都人以黄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谓之‘黄贼 *** 贼’。”这豆屑既可以做饼和蒸食,又需要“熬”制使用,豆渣做不到这些,只能是今天的“豆粉”“豆面”之类,并没有脱去蛋白质。对此结论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清人曾记载一个断案故事:“黄洽中为乌程令,有豆商、米商共争一斛,洽中曰:‘两家构争,皆斛罪也。’叱杖之,斛破,豆屑出焉,乃罪米商。”这里的豆屑显然不是磨制的豆渣,而是大豆的粉末,清代豆浆已风行,此时“豆屑”仍未有“豆渣”之意。
同时古人早已有大豆加水煮熟的食用 *** ,即为“豆羹”。著名的《七步诗》详细记述了“豆羹”的 *** 过程:“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该诗见于《世说新语》,无论是否为曹植所作,均可 ***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对于“豆羹”的理解,可见这种豆羹是将大豆直接放在“釜”中煮烂而成的。从“羹”字本义可知“豆羹”应当是不过滤的,该诗下句“漉菽以为汁”,“汁”或许与“羹”对立为两种食物,但也反映出此时在上层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过滤大豆直接饮用“豆汁”的做法。无论过滤与否,“豆羹”是直接煮大豆的食品,并非豆浆。
这里的“豆汁”在《齐民要术》中有详细介绍:“更煮豆取浓汁,并秫米女曲五升;盐五升,合此豉中。以豆汁洒溲之,令调。以手抟,令汁出指间,以此为度。”与《七步诗》中为同一物,均为煮豆后获得的汁。葛洪《肘后备急方》亦有饮用“豆汁”的 *** :“小豆一斛,煮令极烂,得四五斗汁,温以渍膝已下,日二为之,数日消尽。若已入腹者,不复渍,但煮小豆食之,莫杂吃饭及鱼盐。
又专饮小豆汁。无小豆,大豆亦可用。”这里表现服用小豆亦用煮。同书亦有“大豆汁”制取 *** :“大豆一斗,熟煮,漉饮汁及食豆,不过数度必愈,小豆尤佳……大豆一升,以水五升煮二升,去豆,纳酒八升更煮九升,分三四服。”此类用法非常多,均为直接煮烂大豆,然后过滤掉大豆服用“豆汁”。“熟煮”的过程中,部分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能够脱离大豆溶于水中,这样得到的“豆汁”,从其成分来看与今日的豆浆接近。但两者 *** 工艺不同:一为煮食,一为研磨。
《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这是中古时期唯一一次出现“豆糜”这个词,该文字之后的注文中谈到:“今州里风俗,望日祭门户。其法先以杨枝 *** 于左右门上,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糕糜 *** 箸而祭之。”这里似乎将“豆糜”分开解释为“豆粥”“糕糜”。《荆楚岁时记》本身就是记载风土习俗的书籍,作者将豆粥称之为“豆糜”,可能是地方 *** 的称呼,因此非常少见。由于“糜”字的含义即是粥,所以无论是“豆糜”还是“豆粥糕糜”,相关研究大多将其视为“豆粥”。
豆粥是直接将完整大豆放入水中煮熟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可以佐证:“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都督曰:‘豆至难煮,唯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石崇想喝豆粥很快就能喝到,是因为他的下人提前将其煮熟再做成“豆末”,这里“豆至难煮”表明一般情形之下的豆粥,正是直接将大豆置于水中煮熟,因其体积较大而需要较多时间。
综上所述,中古时期有许多疑似为豆浆的食品,经过分析史料能够得出,豆饧、豆饴、豆羹、豆汁、豆糜与豆粥,都与今日所饮之豆浆有明显差别。
孙思邈记载:“捣赤小豆五合,水和,取汁饮之一合良,滓涂五心。”这里需要注意一点:是“捣豆”中就加入水,还是先干磨,再加水泡出浆?如果是前者,那就是用赤小豆制成了豆浆;但从语序来分析,更有可能是先干磨再泡出浆,与此后的豆浆不同。相对于葛洪煮烂赤小豆的 *** ,这里已改为研磨后饮用,只是没有加热。该文后也涉及大豆加工:“浓煮大豆汁涂之良,瘥亦无瘢痕。”却与葛洪服用大豆的方式类似,也是直接“煮豆取汁”。孙思邈为何对于大豆和赤小豆的处理 *** 不同?一方面大豆比赤小豆体积要大,加工会更有难度;另一方面,这表明中古时期的人们早已注意到大豆中物质的重要价值,但并没有研磨大豆饮用的习惯,连医家用 *** 都尽量不采用研磨 *** 处理大豆。
《证类本草》引《唐本草》中有:“中者,研生绿豆汁,饮一、二升解之。”这一记载较为明确,就是生的绿豆浆,其工艺与豆浆已经非常接近。但这里是生食,又使用绿豆,由于中医临床实践中对于 *** 物的处理有一套独特理念,因而也不能据此认定已将豆浆作为日常食品。不过,我们能够从葛洪以来处理大小豆 *** 的变化,注意到研磨技术逐渐被 *** 物加工吸收借鉴。
从“豆屑”的 *** 可以得知,古人早已具备研磨大豆的技术能力,能够将其磨成“豆屑”,便能够将其磨成豆浆与豆渣。同时,饮用“豆汁”说明此时已具备过滤与煮食的技术能力。这表明古人已经具备了 *** 豆浆的全部技术基础,也是许多学者认为“豆浆早已有之”的主要依据。但文献反映出,人们一直坚持使用“煮烂”的 *** 获取其中的营养物质,并没有诞生豆浆。这一点王利华在研究豆腐起源时已经指出:“我们发现中古以前国人解渴主要是饮浆,在那时的文献之中见过用不同材料做的许多名目的‘浆’,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一条材料反映汉唐之间人们磨豆煮浆饮用。”虽然只是一种初步判断,未展开深入探讨,但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看到磨豆、煮浆、饮汁三种做法,却的确没有发现“磨豆煮浆饮汁”共同发生的饮食习惯。豆浆成为饮品并广为人知,还需要到中古之后的宋元时期。
四、关于豆浆的明确记载
事实上,“豆浆”此物的出现与其成为广泛食用的饮品,应当是两个阶段。前文谈到,古人早已具备制取技术,因此饮用豆浆成为生活习惯只是时间问题,但需要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其推广开来,最终实现这一结果已经迟至元代。
《外台秘要》曾引《经心录》中“豆浆粥”的做法:“右二味作散,和鸡子七枚,令熟并 *** 作丸,煮赤豆作浆粥,服三十丸,日三服。若渴,饮豆浆粥。”这里“煮赤豆作浆粥”表明应当是直接煮烂赤豆,未经研磨。此后,明清之际的谈迁详细记载了北京地区“豆浆粥”的做法:“都肆中以豆屑杂少米煮之如薄糜,晨哺一二瓯,最补元神。”这里使用豆屑,可能是因为大豆直接煮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煮烂,用豆屑可以有效降低成本。从唐代至清代,“豆浆粥”的概念可能发生变化,但从史料分析都不是将豆浆加入粥中,而是直接煮豆使其中的蛋白质等物质析出。
唐末《四時纂要》谈到:“吐甚者,即研小绿豆浆服之,即止。”缪启愉先生如此点读,但此处是“即研小绿豆,浆服之”还是“即研小绿豆浆,服之”,两种理解存在明显的差异。前者很可能获得干的豆粉,也可能获得糊状的“豆泥”,但缺少过滤过程,直接加水服食。如果是后一种理解,即饮用过滤后得到的生豆浆。无论作何解释,均与后世的“豆浆”有一定差别。
宋代豆腐已经广泛出现于食谱之中,陶穀《清异录》中也有对豆腐的明确记载。袁翰青等学者认为豆腐是在食用研磨豆浆后发明的,按此思路,宋代有豆浆已不证自明,但史料中并没有出现饮用豆浆的记载。《证类本草》引《太平圣惠方》云:“以桑柴灰热汤淋取汁洗头面(以大豆水研取浆,解泽灰味,弥佳)。”这里是将大豆加水研磨,然后过滤得到“浆”,记载十分明确,与今日生豆浆并无差别。但其用途是冲洗脸上的灰,并不饮用。同时,《本草衍义》中描述大豆“又可硙为腐食之”,“硙”即研磨,应是磨豆浆做豆腐,仅介绍了大豆可以 *** 豆腐,没有谈到豆浆。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日常生活中并不将豆浆作为食品,而只是豆腐 *** 过程中的半成品。高启安也已提出,豆腐未必是豆浆制成,可以用豆粉。煮烂大豆后过滤得到的“豆汁”,由于其成分与豆浆近似,亦可作为 *** 豆腐的原料。因此,尽管此时豆腐已经明确出现,但仍不能以豆腐的出现作为豆浆成为食品的证据。
元 *** 始豆浆成为广为人知的食物,能够看到较多确切记载。刘时中有曲《端正好》,其中写道:“或是捶麻柘稠调豆浆,或是煮麦麸稀和细糠。他每早合掌擎拳谢上苍。一个个黄如经纸,一个个瘦似豺狼,填街卧巷。”这里应该是将麻、柘两种植物的叶子捶打后混入豆浆之中,由于该曲是为反映饥荒情景,豆浆也不可能过滤,因此是“稠调豆浆”。此外《世医得效方》记载:“上用桑枝灰一斗,热汤淋取汁,洗头面。次用大豆及绿豆浆添熟水,三日一浴,一日一洗面。”此是前引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水研取浆”的 *** ,但这里已经简化为“大豆及绿豆浆”,可知“豆浆”之含义已为人所共知,不需要再多加解释,说明豆浆成为日常生活常见食品。
此外,《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一件关于农夫“司大”的故事,其中有一细节:“司无以为养生计,即所偿钱为豆乳酿酒,货卖以给食。久之,不复乏绝,更自有余。”宋代以后,豆腐和豆浆都会被称为豆乳,能够酿酒的显然不会是豆腐,而是豆浆。这里还揭示出此时已有人卖豆浆为生,表明豆浆在社会上得到广泛食用。《名山藏》记载明 *** 国大将汤和,在参加红巾军之前,也是以卖豆浆为生。
据此,元代豆浆已经进入日常生活中,社会下层未必有能力经常饮用,但已对这种食品不陌生,许多人以卖豆浆为生。食品的推广需要一定时间,豆浆很可能在南宋中后期已成为食物,到元代普遍推行并进入到文人的笔下,将豆浆开始食用确定在宋元时期较为合适。
这里有几条记载需要作出辨析。一是《疮疡经验全书》中谈到涂抹生豆浆:“右为末,生豆浆调匀,搽四向空, *** 毒气时用余浆润之,以助 *** 力。”该书一直署名宋代名医窦汉卿,相关研究认为该书应当是明代的窦梦麟以家传善本及 *** 窦楠的验方为基础,校勘而成,窦梦麟并非窦汉卿的直系后人,其家传善本最早可追溯至元末明初的窦良茂。由此从知识来源的角度看,这一豆浆用法应为明代形成。二是《李师师外传》中写李师师婴儿时只能吃“菽浆”:“寅妻既产女而卒,寅以菽浆代乳乳之,得不死。”菽浆即为豆浆。李裕民列举了书中诸多不合宋朝事实之处,指出应为清初明朝遗民所作。
“菽浆”一词在文献中非常少见,明代中后期之前从未出现,也为判定此书并非宋人作品提供了新的证据。三是《大金国志》中常被引用来描述女真人早期生活方式的一段话:“饮食甚鄙陋,以豆为浆,又嗜半生米饭,渍以生狗血及蒜之属,和而食之。嗜酒,好杀。酿糜为酒,醉则缚之,俟其醒。不尔, *** 。”其中“以豆为浆”的记载,一直被理解为金人爱饮豆浆,甚至有学者提出在金朝建立后 *** 开始模仿女真人的生活习惯,喝豆浆成为一时之尚。同时,《三朝北盟会编》中亦收录一段类似叙述:“其饭食则以糜酿酒,以豆为酱,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芼以芜荑。”许涵度校正时在其后曾注“删以半至此二十四字”,可知“以豆为酱”四字应属原文内容,并非许氏擅改。过去有关金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可能由于史料太过缺少,因此研究者大多选择两者均采信,金人既用豆制豆浆,也用来做酱。
有学者曾注意到这一问题:“这里的‘酱’,有版本作浆,但似应作‘酱’。”仅对其做了推测,未及展开。从内容上来看,两种叙述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酿酒、半生米饭、渍狗血等要素具在,只是排列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因此两种记载中有一种为误,两说不可并存。《三朝北盟会编》成书更早,《大金国志》中这段叙述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三朝北盟会编》中的相关内容,只是在编纂、传写或是刊刻 *** 现了讹误,误“酱”为“浆”。故而不能以此认定女真人已有服用豆浆的风俗,南方后来出现的饮用豆浆习惯,也不能视作受到少数民族影响。
五、余论:饮用豆浆与“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
实物与文字记载两方面均显示,古人早已拥有制造豆浆的技术能力。研磨豆浆并煮食的技术基础并不复杂,最晚在汉魏时期就能完全实现。那为什么豆浆一直到宋元时期才成为日常饮食呢?这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既能更新我们对技术基础与发明出现两者关系的认知,又能进一步看到技术创新与技术推广之间的关系。
豆浆,如果我们将其作为饮食中的一项技术发明,那么它的 *** 工艺应当由几项关键技术构成:技术一是研磨大豆,技术二是将残渣与液体分离开,技术三是煮食。事实上,缺少任意一项都使其与食用豆浆有明显的距离,上文已经述及,这三项技术均有较早的明确记载,但“豆浆”这一发明的完整出现却要迟至宋元时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往往认为当技术基础成熟之时,即可作为新发明出现之日,此前对豆腐与豆浆的研究均存在这种问题。
已有许多研究在思考这一现象,如王利华指出:“科学技术史上的众多事实表明:将若干单项技术联结起来,集成为另外一套新的彼此配套的复合技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发明创新过程,常常需要经过长期摸索才能实现。”本文的结论即可证明,技术基础与发明出现不具有明确的关系,即使在技术基础全部成熟并得到应用的情况下,依然有可能相隔较长时间才出现技术创新或发明。
同时,宋代已经出现豆腐,史料中有不少磨豆制豆腐的记载。未点卤之前的豆腐就是豆浆,可以认为技术发明已经出现,但人们一开始并没有将其视作一种饮料,更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食品。于是乎出现了日常生活中食用豆腐早于饮用豆浆几百年的历史现象,这与我们既往的认知颇为不洽,一定程度上也 *** 了豆腐起源研究的开展。同时,研磨大豆的 *** 一直留存于医疗实践中,长期以来未进入到日常饮食之中,民众还是食用煮豆粥。豆浆之后成为饮品,这项技术恐怕还是从豆腐 *** 工艺中迁移而来。这些现象揭示出技术创新与技术的推广和转移之间同样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实用技术的推广与普及,需要技术之外的社会因素提供力量。
在煮豆粥的时代,其实人们已经注意到,煮烂大豆得到的“豆汁”非常有价值,可将其用于治疗疾病、作为优质饮品。如果先研磨再过滤,显然是一种效率更高的技术,但是普通民众和达官显贵均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古代的下层民众食用豆制品时是不可能放弃豆渣去享受豆浆的,为了获取豆浆而得到副产品豆渣,是一种本末倒置,直接煮食大豆对农事繁忙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更合算的方式。直到几十年前的农村,很多家庭研磨豆浆是不过滤的,连同豆渣一起配上青菜作为主食,这在很多地方被称为“懒豆腐”,其实也符合国人节俭的传统美德,一定要物尽其用。
对于上层社会来说,石崇是很好的例子,煮烂大豆无非是消耗更多燃料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去关心“豆汁”是煮烂还是磨烂的。宋元时期,城市、市镇人口的增加与商业的繁荣提供了豆浆消费的土壤,尤其是豆浆开始作为商品 *** 。在一定规模的经营之下,研磨豆浆显然要比煮烂豆粥成本更低,也能卖出更高的价钱。对于市民来说,一方面远离农业生产,不需要自己从事研磨,另一方面他们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豆浆成为一项日常生活饮食得到推广,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的原因,包括口感、饮食结构、研磨技术等方面,但这一因素最为主要,豆浆可能是作为豆粥的替代品首先受到欢迎。
李昕升提出“中国超稳定饮食结构”的观点,认为国人对于外来作物的接受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嵌入到中国传统的种植 *** 和饮食文化之中。种植 *** 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经济问题,外来作物不能融入原有耕作体系,将导致实际收益的下降。这一判断主要针对外来作物提出,实际上本土食品进入到日常生活,也要考虑到原有饮食结构。大豆是本土传统作物,食用豆制品并不涉及种植 *** 问题。
但豆浆不能得到推广,主要是 *** 工艺带来的经济成本 *** ,在没有庞大消费群体和高效商品交换之前,难以成为日常饮食。相比之下,豆腐能够早于豆浆普及,是因为豆腐是一种素菜,尽管比豆浆的成本还要高一些,但作为菜而不是主食,则又是较为廉价的。其融入原有的饮食结构是比较容易的,各阶层人民都乐于获得这种美味又相对便宜的食品作为菜肴,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主要是想尝试美味,下层人民则为了补充食材的稀缺,因之宋代以后的文艺作品中食用豆腐常被视作清贫的象征。
因此,豆浆 *** 工艺的形成与推广,都不是仅仅由科学技术本身决定的。任何一项技术创新的出现与推广,要到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并产生相应的需求时才能实现。我们将科学技术史分为“内史”与“外史”,梳理内史发展能够看出科学技术自身演进的脉络,但若是不关注社会环境与技术的相互作用,有些现象就难以解释。
最后,揭示豆浆的社会起源对于推进豆腐起源的研究也具有一定价值。前文述及,许多学者站在今天角度上,认为熬制豆浆饮用是豆腐发明的前提,后来者研究豆腐循此思路,陈文华与孙机等人争论的核心为画像石上是不是磨,应克荣等人论证刘安发明豆腐也十分重视石磨。豆腐早于豆浆被食用,表明早期的豆腐未必是豆浆所 *** ,有可能如高启安所推测是豆粉豆面制取,但更有可能是煮豆粥之后对固体成分过滤,再制成豆腐。例如苏轼诗中“煮豆作乳脂为酥”,这里“煮豆作乳”表明是通过煮这个过程获得的“乳”,因而并非研磨好的豆浆,而是煮烂大豆后形成的豆粥,再过滤为“脂”,最终加工成豆腐。豆粥在中古时代十分常见,用豆粉煮汁再过滤则较少。
早餐在家打豆浆,用干黄豆还是湿豆?掌握好3点,豆浆香浓还好喝如今,喝豆浆可谓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要是回看三十年前,并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在家里打豆浆的,那时想喝上一杯浓稠的豆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即使是当下,也会发觉,自家豆浆机打的豆浆怎么也没有早餐店里的豆浆好喝,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以销售豆浆为主要饮品的门店。
要不就是传统 *** *** 豆浆、要不就是使用商用豆浆机打豆浆,既高效还更加美味,怎么都比自己在家里用豆浆机打的豆浆好喝太多,那这是什么原因?
还是说个小故事吧,大家就能知道其中原因,爸妈退休之后,在牛奶和豆浆两种饮品之间做出了选择,觉得还是更喜欢喝豆浆,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在工厂的食堂、街头巷尾的早餐店,来上一杯香浓的豆浆,那种味道早已刻在他们的脑海里,如今退休在家,商场里也有豆浆机销售,实现了他们喝豆浆的 *** ,当然首选豆浆。
豆浆机买回来,黄豆也买了,打豆浆不麻烦,放入干黄豆,加入合适分量的清水,盖上盖子,按下开始键,大约30分钟,豆浆就做好了。
不过在饮用之前,需要经过一道过滤,过滤掉豆浆里的豆渣,然后就可以饮用了,搭配上老妈去早餐店购买的,油条、油饼、热干面、豆皮、烧麦、鲜肉包或者是花卷馒头,早餐吃的是既营养又丰盛。
但是,吃完之后清洗豆浆机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倒不是说又多不好洗,而是豆浆机有一部分不能沾水,导致清洗的时候蹩手蹩脚,活干的不利索,老是担心没有清洗干净。
就这样经过了一周的时间,豆浆机上某几个细小的地方污垢就非常明显了,一家人喝豆浆的时候,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那几处的污垢,影响食欲的同时,还成为了老 *** 心病。
必须要清洗干净,300多元的豆浆机,被老妈彻底清洗干净之后,第二天就不再工作了,电路的地方人为进水坏掉了。
再后来看了几款豆浆机,都好像有这方面的问题,不便于清洗,或者是清洗非常麻烦,之后老妈干脆采用最原始的 *** 磨豆浆,我们家磨豆浆的小号石磨,每年冬季为我们家腌制腊鱼腊肉贡献了全部重量,而用石磨磨豆浆,真不超过3次,是真好喝,但喝上一杯是真不简单,除了需要将干黄豆泡发之外,磨黄豆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买石磨的时候,二老信誓旦旦,权当锻炼身体,可实际上,如果是天天为了一杯豆浆,这么折腾,二老的身体是真受不了。
泡发的黄豆,磨成的豆浆,采用传统 *** *** 的豆浆怎么就比豆浆机用干黄豆打得好喝?早餐在家打豆浆,用干豆还是湿豆好?下文我来给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大家如果也喜欢喝豆浆,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早餐喝豆浆,您最喜欢搭配什么面食,比如:包子馒头还是油条油饼?
一、打豆浆的黄豆是湿豆好,还是干豆好?
首先说说大家使用豆浆机的时候,为什么都会直接选择干黄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使用干黄豆打豆浆更加的简单、便捷,加上豆浆机的机械原理和智能设定,是可以不用泡发黄豆,直接就可以打出豆浆的,简化了 *** 豆浆的步骤,省去了繁琐的泡发黄豆的过程,大家自然会选择豆浆机厂家教给大家的 *** ;
另外,使用干豆打豆浆,相比湿豆来说,节省时间,想喝豆浆的时候不需要等待黄豆泡发的时间,就好似下厨房做饭,我要吃红烧肉,大家肯定是选择最简单的方式,去菜市场或者是超市直接买猪肉回家烹饪,而不会从买小猪仔开始,将猪仔养大后杀猪得到上好的五花肉,然后再 *** 红烧肉。
这个比喻里,大家伙都非常清楚,自家养大的猪,猪肉自然是更加美味可口的,因为这里面有自己的劳动付出,但却不符合实际情况,将猪仔养大需要至少3个月,泡发黄豆至少需要一个晚上,两种方式对比之后,想吃红烧肉的自然选择自己去超市购买五花肉、像喝豆浆的直接选择干黄豆打豆浆,用这样的比喻,大家应该是能够明白的。
再来说说湿豆打豆浆的优势,干黄豆在清水中浸泡的这个过程,3-5个小时的时间,干黄豆中的单宁和植酶会减少,这样黄豆中的蛋白质和各种营养元素才能被我们身体更好的吸收;
另外还有一个效率的问题,用湿豆打豆浆,虽然泡发黄豆的时间比较长,用泡发后的黄豆打豆浆,豆浆料渣少出浆率比较高,营养价值也会高一些。
这里说的单宁和植酶是这么回事,通过泡发,会将黄豆中阻碍矿物质吸收的单宁和植酶等抗营养物质溶出,豆浆中蛋白质含量自然就会高。
泡发黄豆打豆浆都是传统工艺,泡发后研磨时能磨得更细,这样 *** 的吸收效果就会更好。
打豆浆的黄豆是湿豆好,还是干豆好?因为重要的因素是人,人喝豆浆的原因是为了补充营养,其次才是豆浆的口感,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湿黄豆打豆浆更好。
二、喝豆浆时,您忽略了这3件事情?
1、生豆浆是不能喝的,无论您在家是使用传统 *** *** 豆浆,还是使用豆浆机打豆浆,都要保证豆浆是完全煮熟的状态,特别是豆浆机,程序出了问题,看着豆浆打好了,但可能就是生豆浆,所以一定需要再次加热,将豆浆完全煮熟。
2、有一段时间,在家里打豆浆,我经常用保温杯带一杯豆浆到学校去喝,当我不知道的是,豆浆有很好地去除保温杯水垢的效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在清洗保温杯,为保温杯中的细菌提供了很好的营养物质,如果经常喝这样的豆浆,确实是不太好的。
3、喝豆浆吃鸡蛋,好像不太好,传言是这样说的:豆浆中有一种胰蛋白酶 *** 的物质,能够 *** 胰蛋白酶,而鸡蛋含有很多的蛋白质,喝豆浆吃鸡蛋,豆浆中的这种物质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
虽然这种传言不可信,因为煮熟的豆浆,胰蛋白酶 *** 在高温下已失去了活 *** ,不过大家还是要所了解。
三、豆浆机也能用湿豆打豆浆?
泡发黄豆大约需要1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这样才能将黄豆彻底泡透,我们用豆浆机打豆浆的时候,泡发好的黄豆替换成干豆即可。
泡发后的黄豆,用豆浆机打豆浆,你会发觉,这样 *** 好的豆浆,豆渣明显减少,出浆率也会更高。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泡发好的黄豆不要直接放入豆浆机,需要煮熟后再放入豆浆机开始打豆浆,原因在于,黄豆如果没有煮熟,腥味很重,没法喝。
煮熟的黄豆,打豆浆也是需要完全将豆浆煮熟后再饮用的。
四、打豆浆,无论是豆浆机还是传统 *** ,都应该知道的事情?
1、泡黄豆时,大多使用冷水,但我听说过使用开水泡发的,效率高,时间短,大约1个小时,黄豆就可以泡发,可能会损失一大部分黄豆中的营养物质。
2、无论是湿豆还是干豆,无论是传统 *** 还是豆浆机打豆浆,并不是越浓的豆浆越好,过浓的豆浆会对我们的肠胃带来较大 *** ,而且打出来的豆腥味也会更重一些,也并不好喝。
3、6倍的水,是最合适的,浓淡适中,营养价值也高,当然每个人的饮食习惯是不一样的,可能这样也会有人觉得太浓,可以增加至10倍的水,相对来说,味道会寡淡一些,而且打豆浆要用冷水,不能使用温水或开水。
4、豆浆机的选择,可以选择不锈钢罐体的,比塑料的耐用结实,更好在买豆浆机时查看一下是否具有精磨功能,这样的豆浆口感才会更加细腻。
写到最后,还想啰嗦几句,早餐在家打豆浆,用干豆还是湿豆好?掌握好3点,豆浆香浓还好喝,最后总结一下吧:
泡发黄豆打豆浆都是传统工艺,泡发后研磨时能磨得更细,这样 *** 的吸收效果就会更好。打豆浆的黄豆是湿豆好,还是干豆好?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人喝豆浆的原因是为了补充营养,其次才是豆浆的口感,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湿黄豆打豆浆更好。
北京豆汁和河南新乡粉浆饭中的粉浆是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尽量做到恰如合适、通过原创图文,在文字与 *** 之间为您分享一道道菜肴,它们美味、漂亮、营养,您要什么样的美食,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给您!
首先亮明观点,我觉得是。
先说我对豆汁的认识。
上个世纪听的少,见得少, *** 上也没有什么微博、微信、头条、抖音这些灌知识、灌见识的玩意儿,虽然去过几次北京,却从没听过什么豆汁、卤煮之类的所谓北京名吃。北京也有朋友,去了领着你也是去吃涮羊肉、烤鸭什么,吃早饭吃过一次炒肝儿,也不觉得好吃,就是个咸、腥,虽然差不多,个人以为论味道确实比不了咱新乡遍大街的北舞渡或是逍遥镇。
大概2003年去北京找朋友玩儿,住在月坛宾馆。早上顺着北小街往阜成门外大街走,路口有一溜小饭馆,门口支地摊儿。一个朋友发现有油条、豆浆,盛上来喝一口差点儿哕(音yue,新乡话吐的意思)了,酸臭,忙问老板是不是豆浆馊了,才知道喝的是“豆汁儿”——老北京人见人爱的皇家吃食。
豆汁儿,焦圈儿
豆汁是北京独有的吃食儿,是水磨绿豆 *** 粉丝或团粉时,把淀粉取出后,剩下来淡绿泛青色的汤水,经过发酵后熬制成的。据说早在乾隆年间,豆汁已经传入皇家了。"老北京有句话不喝豆汁儿,算不上地道的北京人"。因为豆汁的气味及味道独特,若非长期接触,很难习惯。
喝豆汁儿是有讲究的,首先得烫,偶尔咕嘟着几个泡的热度更好,再者必须得配上切得极细的芥菜疙瘩丝儿、淋上辣油,同时还得搭上两个"焦圈儿",吃起来主味酸、回味甜、芥菜咸、红油辣,五味中占了四味,再加上焦圈儿的脆和香,绝配!
以上引用的是某百科的介绍,当时我们实在是没吃出来“主味酸、回味甜”那一口,再则这早点摊儿上也没什么焦圈儿,就是油条。反正我们都没喝,拿着油条结账走了。
后来又吃了回卤煮火烧,也不好吃,没我们新乡的 *** 杂碎汤泡上烧饼好吃。其实一个地方的人吃什么不吃什么是有“癖”的,我就总觉得,猪大肠就只能当下酒菜吃,或烧或卤都行,万万不能和面食弄在一起,容易把大肠的本味给传出来。
卤煮火烧
烧饼泡进杂碎汤
当然了,“百货对百客,百味对百人”,我觉得难吃、难以下咽,别人可能就甘之若饴,这没什么奇怪。就像我们吃捞面条喜欢就瓣大蒜,觉得奇香绝配,有人却认为奇臭难当、避之不及。
同样,对待粉浆饭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为什么接受了粉浆饭。
粉浆饭在河南最有名的当属安阳和洛阳,新乡都是学人家的。但新乡的粉浆饭主要学的是洛阳,也就是“浆面条”。安阳粉浆饭用小米,新乡粉浆饭用面条。
之一次吃粉浆饭是在1983年去洛阳找同学,当时和后来之一次喝豆汁儿感觉一样,酸、臭,差点儿哕了。但是,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好,即使恶心也不舍得扔了,呼噜呼噜勉强吃进去,生怕拉肚子。
从此就对粉浆饭有一种抗拒心理,直到有一年在劳动桥下沿吃了一回新乡的粉浆饭,这种厌恶才渐渐平复,以至于现在好久不吃还想得慌。
那个时候劳动路刚刚从劳动桥打通到平原路,卖粉浆饭的是推个三轮车,在劳动桥下沿,不在路东,在路西,大概是现在中原银行的前面那一块儿。
劳动桥桥南西南角中原银行
前一天晚上喝多了酒,睡在了澡堂,大早起起来,饿的前心贴后心,酒劲还在,头直发蒙。一起的朋友建议就近劳动桥头吃碗粉浆饭再去上班。那时候卖早点的不多,除了新荣街、 *** 路杂碎汤和车站附近卖豆腐脑、胡辣汤、稀饭,其他就近的地方还真不好找。
但这新乡的粉浆饭却很对我的胃口,酸,但不臭。卖相不好,也有一股剩饭味儿,但绿豆面味儿很浓,有面香,据说里边加的是红薯叶,再舀上一勺芹菜丁,糊糊涂涂却又口感清爽,酸酸的喝下去胃里很舒服,特别适合喝多了以后食用。吃过以后到了单位竟没人闻出我嘴里酒味,哈哈,真是奇物啊!
劳动桥粉浆饭跟这差不多,因是绿豆面条,颜色稍重。
由此一念,举一反三。我从一个反对者变成了粉浆饭的拥趸。每当晚上喝多了酒,第二天一早必去找粉浆饭吃。或者喝了酒当时就吃,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兄弟们常去清雅阁洗澡,出来后门口一人一个烧饼夹猪头肉,一碗粉浆饭,再来半斤酒,超得劲。清雅阁粉浆饭用的是机轧白面条,差了点意思。不过,只要没有臭味,酸酸的,咋都好吃。
我 *** 知道了,就说,在家里做吧,总比外边卫生。
外面的粉浆饭怎么做的我不知道,我们家的粉浆饭是这样做的。
我们家的粉浆饭。
粉浆饭的灵魂就是粉浆,粉浆就是做绿豆粉皮、粉丝的副产品,和豆汁儿一样也是磨了豆子、出了粉芡、粉皮以后留下的汤水,经过发酵、变酸而成。自己做浆太麻烦,肯定划不来。那就去买现成的。
新乡市有个卖粉浆的,原来在漂染厂西面,现在搬到了姜庄街。买粉浆时一定要闻一闻是不是味儿正,这需要经验,因为要我去买,咋闻都是酸臭的。
凡做粉皮的都有粉浆
我们家俩人吃,买1块钱的浆就够了,再买8毛钱的二细面条和一颗芹菜。先把粉浆放锅里煮开,等浮沫熬出撇净,放入芹菜叶、熟黄豆或花生米,适量放盐,煮一会后儿下面条。然后宽油葱花炝锅,倒进去,多搅搅,让油和浆面充分融合,起锅OK。
吃的时候,把芹菜梗切成小丁撒点盐,一起上桌。
俺家粉浆饭跟这差不多,但这个花生米太多了,容易喧宾夺主。
吃粉浆饭我还行,虽然原料一样,豆汁儿估计我还是无法接受。就像我可以吃王致和臭豆腐,却接受不了街上的炸臭干子一样。每逢闻到飘过来一股一股的不可理喻的那种味道,就一个字,想哕。
(纯属个人经历和感受,没有对任何食物不敬的意思,若本文无意冒犯了哪位,敬请告知,马上改正。)
您想更多了解粉浆饭的一些趣事,请在以下搜索中搜索“粉浆饭”。
三分钟带你了解大豆大豆
大豆,包括黄豆、黑豆、青豆,就是能单独打出豆浆或磨出浆的豆类。
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是豆腐、豆瓣酱,这些都是大豆制品,包括非发酵豆制品(豆浆、豆腐、豆腐干、豆腐皮、豆腐片、豆腐丝)和发酵豆制品(豆豉、豆瓣酱、豆汁、纳豆、腐乳)。
经常吃豆类有什么好处?大豆含优质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钙、B族维生素和植物化学成分,例如: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维生素B12和大豆低聚糖,其中大豆低聚糖是双歧因子,促进双歧杆菌的增长,维护肠道环境。
(来源: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